当代艺术与互联网之间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号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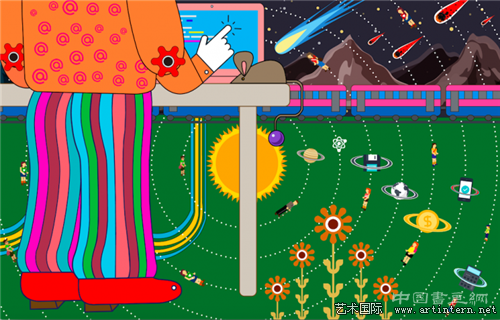
在“互联网+”浪潮狂野地席卷各个行业之后,如今正过境一向对技术慢热的当代艺术圈。过境之后,会是一片残花败柳还是蓬勃生机?从2000年初开始的艺术品电商,到微博时代,再到时下名目繁杂的App、微信自媒体,再到依托互联网的创作形态……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纵横捭阖在频繁上演,造梦的尖叫声挤满了视听空间,互联网冲动的荷尔蒙弥漫在当代艺术空气中,它看似在毫不留情地重塑着这个世界。然而再喧腾的景象也会经历尘埃落定的过程,繁荣之下,我们尚未看到几个专业性、戳中痛点和盈利模式清晰的“互联网+”产品,真正能联结过去与未来,具备持久发展潜力的模式与业态尚未“水落石出”,“当代艺术+互联网”正身处十字路口,忐忑不安和雄心万丈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时代症候。
交易规则无线上线下之分
2000年,艺术品电商先驱嘉德在线正式成立,这个时间比淘宝还早了三年。嘉德在线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少藏家开启收藏之路的初次试水地,也是许多年轻艺术家收获第一桶金的窗口,甚至有艺术品经纪人在该网站上发掘过艺术家。彼时的互联网还是一片广袤的处女地,谁先踏入,谁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第一。但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在当代艺术的艺术品电商步伐几乎停滞不前的前提下,历经十六载的嘉德在线却因假画等商业规范问题,错失了成为艺术品电商龙头老大的良机。
怀揣着对艺术消费的憧憬,以及风险投资的介入,2010年后艺术品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HIHEY、易拍全球、一点儿艺术、艺典中国、艺客网、阿波罗、艺术狗、宝甄网等以网站或App的形式横空出世,这里也成了一块吸金宝地。但潮起潮落也成了它们的常态,比如“一点儿艺术”在一年内凭借突破100万的注册用户迅速蹿红,本以为它能成为中国第一个纯粹意义的艺术品电商,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辉煌的过往瞬间成了过眼云烟,淹没在电商大军中。这些势如破竹的艺术品电商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由于对艺术市场的过高期待,导致定位的不清晰,影响用户黏度,再加上专业服务无法及时跟上等软肋,使得这一奢侈消费,降格为屌丝消费。尽管互联网的介入,给艺术圈增加了新玩法,但是从一门生意来看,并无线上线下之分,拼的都是眼光、资源、经验、品牌、信誉。再加上互联网终端产品逐渐趋于同质化,互联网+当代艺术产品也必将经历一场优胜劣汰的洗礼。
喧嚣之下的冷酷现实
行业外对艺术市场这块“肥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想象,很多人都想来分一杯羹。与传统画廊、拍卖行的经营方式相比,电商的优势在于成本低、门槛低、方便交易。在专业的艺术品电子商务平台纷纷建成之时,非艺术品领域的电子商务大鳄们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亚马逊、eBay都是最常被提及的案例。亚马逊在1999年尝试推出艺术品线上销售以失败告终后,于2013年卷土重来,推出了拥有四万多件商品的在线艺术馆,既有44美元的一幅猫的画像,也有高达485万美元的诺曼•洛克威尔《威利•吉利斯:家里送来的包裹》。eBay则与苏富比联手,同样在经历夭折后,于2015年再次推出网络拍卖平台。这两个案例透露出一个重要数据——现阶段主打的基本都是在一千到五万美元之间的艺术品。国内知名电商苏宁易购于2013年搭建的艺术品拍卖频道,每周推出2-3个拍卖专场,但其拍卖基本无人出价,2015年便停止了该业务。栽的这一跟头表明非专业电商大佬既高估了自己的先天优势,也高估了中国互联网中的艺术购买力。
从媒体人到市场交易实践者的胡湖就曾总结说:“艺术品电商的鼓吹者有一个原罪:误让人以为艺术品在网上存在一个很大的增量市场,误让很多卖不掉画的艺术家和机构以为网上就可以卖掉。事实上这个增量市场不存在,这些线下卖不掉的画在网上同样卖不掉。艺术品电商给了很多这样的卖家希望,等他们真的参与了交易,才发现现实依然是冰冷的。”至少从目前来看,在艺术品电商的喧嚣之下,还没有一份像样的成绩单。
微拍的生意经
相比网站、App这类成本投入巨大的电商,搭载微信平台的微拍则进一步消除了交易壁垒,使得交易随时随地可能发生,也更接地气。2013年年底,双飞艺术小组率先成立了“中国最好的拍卖协会”;紧接着“活在未来的艺术行业观察员”胡湖成立了阿特姐夫日夜场;此后又陆续出现蔷薇拍卖、大咖拍卖等微拍群。还记得马年的那个春节档,几乎都是被这些满天飞的微信红包群所占据。“社交+红包”的模式已经从节假日引爆点,完成了向日常长尾的延展覆盖。两年多的时间过去,在微拍这场持久战中,目前仅有阿特姐夫日夜场还处于活跃状态。作为对主流拍卖行的补充,微拍业务范围与后者几乎不构成交集,作品大多是无底价起拍的低价位的当代艺术品。阿特姐夫日夜场目前为止落槌价最高的是35.8万元的草间弥生《碟》。
作为互联网介入得最广的艺术品交易环节,基本模式仍锁定在将线下的交易场所转移至线上,游离在低价位区间。不过最近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如artand、宝库这一类的垂直社区型App。这类的尝试能否成为电商的突破口,我们拭目以待。
新媒体商业价值转化的解决方案何在?
在心理承受能力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当代艺术圈曾流行过几位匿名的网红:比如微博时代的阿特姐姐、独眼狙击手的眼睛;豆瓣上的一杯生普洱、66号高速公路等,他们可以视为微博时代的自媒体。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媒体往往是指依托于微信平台、独立于机构之外的个人化媒体。“天下一叔”据说是位有过拍卖公司从业经验的女子,虽然推送频率缓慢,但对数据的敏感也圈住了一批粉丝;“艺术绘画坏蛋店”凭借坏蛋店主邸小伟个人独特的“坏”基调推送绘画作品,既成为坏蛋店的标签,也成为店家不可替代的特质;自称用镜头写作的Action Media,则依靠视频霸占了当代艺术圈的小屏幕。传统艺术媒体如《Hi艺术》、《艺术新闻》、雅昌艺术网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在全力避免掉队,在微信端这个主流舆论阵地的传播链条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如果说传统媒体依靠广告、增值服务盈利,新媒体靠社群经济、网红、电商来风生水起的话。那么就当代艺术圈而言,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的互联网转型都没能跳脱出传统的盈利模式。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自媒体出身的Papi酱以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在两个月内迅速走红,并且其视频贴片广告以2200万元成交。比起人家动辄百万起的粉丝群,小众的当代艺术圈却只能沉浸在破万阅读中自我陶醉了。如何将内容转化为商业价值?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摆在媒体面前一个重要问题。
戳中痛点才是王道
当微信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代名词时,也刺激着艺术家、策展人们脑洞大开,但新兴事物的属性也往往容易鱼龙混杂,更多号称“互联网艺术”的作品还停留在小打小闹上,或远离了艺术,或脱离了互联网。所以我很赞同艺术家徐文恺(aaajiao)所言:“回归到作品。我们需要真的互联网作品,不是艺术在互联网上。” 策展人鲍栋在2015年年底发起的“文化馆”线上艺术计划是相对纯粹的项目之一,它以微信公众号作为空间现场,每周发布一位参与者的作品,同时为参与者提供技术支持和1000元的稿酬。
有人说,“互联网+当代艺术”缺乏的是具备互联网思维的人才,这或许没错。但是,当看到一位年仅三十岁的小鲜肉Magnus Resch推出与自己同名的App,并且被Bloomberg推荐说:“这个App将会改变你购买艺术的方式”时。大家认为这位曾经出版过《Management of Art Galleries》(画廊管理)一书艺术市场专家的身上又能有多少IT基因呢?这位有过画廊从业经验,还做过Larry’s List的创始人,借用的正是如滴滴打车、airbnb这些闲置资源的“众包”模式,凭借良好的媒体关系,将每一幅作品的信息、价格统统收录进来,全民共享。Magnus凭借自身的专业敏锐度,戳中了这个行业的痛点,或许这才是对“互联网+当代艺术”的最佳诠释。
在互联网这盘大棋上,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有余,但创新不足。冲动过后,如何发酵?我们更期待看到互联网给这个行业带来更多实质性地改变。正如同微信的崛起让当时如日中天的微博措手不及一样,网络时代工具的更新换代正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迅猛向前。最近,互联网又增添了VR(虚拟现实眼镜)这枚利器,“VR+艺术”没准又将成为下一轮热潮。
